曾经,林子昂是人人艳羡的贵府少爷,而我只是一个烧火丫头。
我被卖进林府的第二天,林大少爷就被罢了官,林老爷也为了给大少爷求情,被贬到南州。
全城嘲笑,他落魄凤凰不如鸡,我却甘心与他共苦,最后竟稀里糊涂被大少爷娶为正妻。
几年后,他功成名就,世家贵女争相攀附,蜂拥而至。
我暗自思量,想着为他纳两门贵妾,或能稳固他的地位。
京城媒婆早已已约好,纳妾之事只待我拍板定夺。
不料,他从扬州风尘仆仆赶回,堵在家门前。
他双目赤红,身子因怒气而颤抖,咬牙切齿。
“你今天敢踏出这门半步试试?”
01
我运气不太好。
刚被卖进林府做丫鬟的第二天,林府就出了大事。
我被卖来时,人牙子得了不少银子,心情好,忍不住多说了几句。
他说林府如今风光无限,能留下来干活,简直是天大的福气。
林府的下人吃得特别好,白花花的馒头随便吃,管饱。
我一口气吃了四个馒头,乐得一晚上没睡着。
可第二天早上,几个小厮用木板抬回一个人。
那人趴在木板上,下身盖着白布,头发乱糟糟的,看不清脸。
好半天才从旁人嘴里知道,抬回来的竟是林府大少爷林子昂。
他被皇帝罢了官,还当众挨了五十下廷杖。
林老爷在朝堂上为儿子求情,结果被贬到南州。
夫人一听这消息,当场晕了过去,喝了四碗参汤才醒过来。
林府上下一片乱糟糟,二少爷又在外地书院读书,家里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。
我悄悄问教我规矩的李婶,廷杖到底是什么。
李婶叹了口气,说:“廷杖就是当众扒了裤子,用大棍子打屁股。”
我听得目瞪口呆。
小时候我淘气,娘气急了,也会拿草鞋打我屁股,教训我听话。
可那毕竟是小时候的事。
如今林子昂都二十多岁了,怎么还能被当众打屁股?
还是脱了裤子打,羞也羞死了,他怎么受得了?
虽然我刚来林府,但关于大少爷林子昂的传闻,已经听了一耳朵。
林老爷官职不高,只是七品小官。
人牙子说的风光无限,全靠大少爷林子昂。
林子昂是个读书天才。
他四岁开蒙,过目不忘,二十岁那年连中三元,名震京城。
本朝开国以来,还没人能连中三元,更别说他那么年轻。
皇帝破格提拔他,让他辅佐太子。
如今林子昂二十三岁,已经是太子身边的得力助手。
大家都说,等太子登基,林子昂封侯拜相不过是早晚的事。
可现在,林府的天塌了。
府里死气沉沉,到了晚饭时间,那么大的宅子,竟没人说话。
我被这压抑的气氛吓得连馒头都不香了,只敢吃两口就放下。
林子昂被抬回来时,下身盖着白布,可血流得太多,白布都粘在他身上了。
那天晚上,林府把京城有名的大夫都请来了。
药童提着药箱进进出出,忙得脚不沾地,整个院子弥漫着草药的苦味。
听说是要保住林子昂的腿,别让他落下残疾。
下人们私下议论,林子昂惹怒了皇帝,连太子都保不住他。
没人知道金銮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有人说林府要被抄家,有人说要灭族,还有人说要诛九族。
我吓得心惊胆战。
刚来林府,我还摸不清情况,夜里不敢睡觉。
闻着空气里的药味,我迷迷糊糊地想,好好的日子,怎么就到这地步了?
李婶睡在我旁边,见我翻来覆去,叹了口气,从怀里掏出个馒头递给我。
“傻丫头,拿着吧,以后可不一定吃得上了。”
林府这光景,确实不一定吃得上了。
我接过馒头,舍不得吃,悄悄塞到枕头底下。
熬到天亮,管家吴叔代夫人召集了府里所有人。
吴叔宣布了一件事,林府要遣散一批下人。
想走的,都有好去处的,林府会还卖身契,每人再给十五两银子。
想想也对,林府现在不比从前。
林子昂要治病,二少爷要读书,夫人要养病,林老爷去南州还得花钱打点。
处处都要用钱,养不了那么多下人了。
林府有林府的难处,可我也有我的难处。
我才十四岁,跟着人牙子来京城,出了林府,我谁也不认识。
天大地大,林府倒了,我好像也没别的去处。
我总不能刚拿了卖身契,又去找人牙子把自己卖了吧?
所以我留了下来。
李婶却走了,她攒了点养老钱,听说外面还有亲戚可以投奔。
她临走前,把她常用的针线盒送给了我。
林府家大业大,一夜之间散得七零八落。
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六个人,我是年纪最小的。
除了我和吴叔,还有夫人院里的翠儿、大少爷的近侍阿福、马厩的张七,还有府里的老人周大爷。
周大爷无儿无女,早把林府当家,主动陪林老爷去南州。
山高路远,林老爷身边总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照顾。
至于林府这边,翠儿是夫人的人,自然不能动。
林子昂伤了身子,身边得留个男仆方便伺候,阿福就留下了。
吴叔继续管家和管账。
剩下我和张七,张七负责打扫院子。
我呢,本来是帮李婶烧火择菜的,她一走,厨房没人管了。
吴叔看着我,眼神有些犹豫。
我知道他觉得我太小,怕我干不好这活。
再说,我刚来,他也不了解我的为人。
可林府不要我,我又能去哪儿?
我咬咬唇,对吴叔说:“我在家常做饭,要不先试试,不行再换人。”
我留下来,已经证明我对林府的忠心。
这时候再买新丫鬟,林府这光景,怕是挑不到好人。
吴叔想了想,点头同意了。
接下来的日子,林府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,连空气里都透着股冷清。
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生火烧水,准备早饭,忙得像个陀螺转个不停。
厨房里只有我一个人,锅碗瓢盆叮当作响,偶尔还能听见翠儿在院子里低声啜泣。
她是夫人的贴身丫鬟,夫人病了,她整日提心吊胆,怕夫人撑不过去。
我偷偷瞄过几次,夫人躺在床上,脸色白得像纸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翠儿说,夫人从醒来后就没吃过一口饭,只喝了点水,眼神空洞得吓人。
我心里也跟着发慌,但手上的活不能停,米要淘,菜要洗,柴火得添。
好在我在家时常帮娘做饭,手艺不算顶尖,但对付几个人吃饭还是够的。
吴叔尝了我做的饭,皱着眉点了点头,说:“还行,凑合吃吧。”
这话听着不怎么好听,可我还是松了口气,至少厨房的活我保住了。
林子昂的情况更糟,听说他醒了,但整个人像是丢了魂,话都不说一句。
阿福守在他床边,端茶送药忙得满头大汗,可林子昂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
我偶尔路过他房间,透过门缝看见他躺在床上,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。
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少爷,如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,真是让人唏嘘。
下人们私下议论,说林子昂可能得罪了朝中某位大人物,才落得这下场。
有人猜是太子身边的另一位重臣嫉妒他,暗中使了绊子。
还有人说,林子昂在朝堂上直言不讳,触了皇帝的逆鳞。
我一个小丫鬟,哪懂这些朝堂上的弯弯绕绕,只觉得林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
有天晚上,我在厨房熬药,药罐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院子里却安静得吓人。
突然,翠儿跑进来,脸色苍白地说:“不好了,夫人又晕过去了!”
我吓得手一抖,差点把药罐子打翻,赶紧跟着她跑到夫人房里。
夫人躺在床上,嘴唇发紫,气息微弱,像是随时要断气了。
吴叔已经派人去请大夫,可夜深人静,大夫来得再快也得等上一会儿。
翠儿急得直哭,嘴里念叨着:“这可怎么办,夫人要是去了,林府就真完了。”
我站在一旁,手足无措,只能帮着烧热水,递帕子,尽量不添乱。
好不容易大夫来了,开了方子,抓了药,夫人总算缓过一口气。
可大夫走时,悄悄对吴叔说,夫人这是心病,药只能治标,治不了本。
我听了这话,心里更沉重了,林府这艘大船,像是随时要翻。
第二天,吴叔把我叫到一边,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,里面是几块碎银子。
他说:“丫头,你干得不错,这点银子你拿着,攒着点用。”
我愣住了,没想到吴叔会给我银子,毕竟林府现在处处都要花钱。
我推辞了几句,可吴叔摆摆手,说:“拿着吧,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”
我攥着那包银子,心里五味杂陈,既感激吴叔的信任,又害怕林府的未来。
那天夜里,我又闻着药味睡不着,翻出枕头底下的馒头,咬了一口。
馒头已经硬了,嚼在嘴里干巴巴的,可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我想,不管林府以后怎么样,我得先活下去,活下去才有希望。
几天后,传来消息,林老爷已经平安到了南州,但那边条件艰苦,吃饭都成问题。
周大爷来信说,林老爷瘦了一大圈,整日唉声叹气,像是老了十岁。
我听着这些,心里酸酸的,林府从前的风光,如今只剩一地鸡毛。
可我一个小丫鬟,能做的也只有把厨房的活干好,让留下来的人吃饱饭。
我开始学着做些新菜式,尽量让饭菜有点味道,免得大家吃得太寡淡。
张七有时候会帮我劈柴,嘴里还哼着不知哪学来的小调,倒是给厨房添了点生气。
阿福偶尔也会过来,偷拿个馒头,笑着说:“丫头,你这手艺比李婶还强。”
我被他逗得脸红,赶紧低头淘米,不敢接话。
林府虽然冷清,但我们几个留下来的人,像是拧成了一股绳,互相照应着。
我开始觉得,也许林府还有翻身的日子,只要我们不放弃。
可就在这时候,京城里又传来了新消息,说太子也因为什么事被皇帝责骂了。
林子昂的事,好像还没完,像是有一张大网,慢慢把林府罩住了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,看着天边黑压压的云,心里隐隐觉得,接下来的日子,恐怕更不好过了。
02
就这样,十四岁这年,我稀里糊涂成了林府的厨娘。
也多亏林府落魄了,不然那些名贵食材,我连见都没见过。
我负责一天三顿饭,早上简单,煮点粥、蒸点包子就行。
中午和晚上麻烦些。
夫人吃素多年,身体又弱,如今病了,每天得喝一碗燕窝粥。
幸好燕窝粥是翠儿亲自做的,我不用操心。
林子昂受了伤,正需要补身子,我得给他炖鸡汤、熬排骨。
主子的饭做好,还要准备下人的饭,菜式得有点区别。
我每天起得很早,先把林子昂的汤炖上,再熬粥、做饭。
不是在洗碗,就是在择菜,忙得团团转。
也不知道是不是夫人和林子昂胃口不好,我做了几天饭,没人说我做得不好。
主子不吭声,吴叔自然也不说话。
过了几天,见吴叔没找我,也没打算买新丫鬟,我才松了口气。
张七人不错,闲下来会帮我劈柴挑水。
他负责打扫院子,到处跑,不像我只能待在小厨房里。
他在林府待了三年,知道的事比我多。
他告诉我,林府以前风光的时候,简直了不得。
每天都有穿金戴银的大人物来拜访,求见林子昂。
有时候帮那些人带个路,都能得一把金瓜子赏钱。
林府的主子心善,从不随便打骂下人,月银也给得多。
在林府干几年,只要有点心计,都能攒点钱。
攒够了钱,投奔亲戚也好,回乡开铺子也好,总比做下人强。
我忍不住问张七:“那你为什么不走?”
张七愣了一下,支吾道:“林老爷对我有恩,我得报答。”
至于什么恩情,他没细说。
他岔开话题,继续讲林府的辉煌往事。
要说林府的风光,自然离不开林子昂。
林子昂长得一表人才,前途无量。
他还有一桩婚约,定的是永宁侯府的嫡女。
那可是家世、容貌样样顶尖的婚事。
可现在,林子昂出了事,前途毁了,腿伤得重,连能不能走路都不知道。
张七偷偷瞄了瞄四周,低声说:“我看这婚事,怕是要黄了。”
“永宁侯府估计不愿把嫡女嫁过来。”
我心里一紧,也压低声音问:“难道还能退婚?”
退婚的话,永宁侯府的嫡女就不用嫁了。
可这样一来,侯府的名声得多难听?
金枝玉叶的小姐退了婚,以后还怎么说亲?
张七像是很懂得这些大户人家的门道,神秘地说:“不到万不得已,不会退婚。”
“侯府庶女多得很,随便挑一个给林子昂,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我倒吸一口凉气:“替嫁?”
张七没说话,竖起食指,冲我“嘘”了一声。
我也不敢再说了。
心里却忍不住想,林子昂才华横溢,年少成名。
如今落难,永宁侯府若真用庶女替嫁,对他来说,比退婚还羞辱。
白天跟张七聊了太多婚嫁的事,晚上我迷迷糊糊梦见了石磊。
离京城九十里,有个清溪镇。
清溪镇有个白水村。
我家就在白水村,普普通通一户人家。
我爹种地,我娘在村口摆了个卖面条的摊子。
我从小就在摊子上帮忙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
直到我娘去世,爹很快娶了后娘。
后娘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家里多了几张嘴。
爹一个人种两亩地,养不了全家。
从那以后,爹就顾不上我了。
他们打算早点把我嫁出去,最好是去村里王老爷家做妾。
王老爷年纪大,喜欢年轻姑娘,他府上的妾都在十四五岁。
爹和后娘打算等我一来月事,就让我去王老爷面前露脸。
看上了最好,看不上再说。
可我不喜欢王老爷,他比我爹还老。
如果非要嫁人,我想嫁石磊。
石磊是我小时候的玩伴。
他娘卖凉茶,摊子就在我娘旁边。
他爹死得早,全靠他娘养大他。
石磊有哮喘,不像我弟弟那么闹腾,也不像同龄的男孩子那么粗鲁。
他特别安静,叫他吃饭就吃,叫他喝水就喝。
我后娘看不上他,背地里说他胆小。
我嘴上不敢反驳,心里却觉得,世上有人胆大,就得有人胆小。
胆小怎么了?他安安静静的,不会像村里那些男人,喝醉了就打老婆。
嫁给他,我觉得踏实。
石磊不卖凉茶,他跟村里的老木匠学手艺,想做木匠。
我见过他做的凳子,平整光滑,一点毛刺都没有。
那时候我做梦,梦见石磊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。
他提着两只大雁,风风光光到我家提亲。
我在梦里盼着爹和后娘看在他有出息的份上,把我嫁给他。
别让我去王老爷家做妾。
后来想想,那时候我真是想太多了。
王老爷也好,石磊也好,都是好路,哪轮得到我挑?
最后,我走的是第三条路,谁也不想的路。
我最小的弟弟得了急病,拉肚子拉得瘦了一圈。
偏偏那时候,爹去请大夫,山路滑,摔断了腿。
弟弟得救,爹也不能落下。
救命的钱从哪儿来?
我含泪跟人牙子走那天,遇见了石磊。
他坐在家门口,正在削一根竹子。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慌忙低下头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
今晚的梦里,我又梦见他了。
他还是在削竹子,低着头不敢看我。
人海茫茫,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见。
最后一眼,他都不肯看我。
看我一眼又怎样?我不会让他倾家荡产买我。
我只想好好跟他道个别。
后娘说得对,他太胆小了。
梦醒后,我摸了摸枕头底下,掏出那个硬邦邦的馒头。
这里是京城林府,我签了卖身契,是林府的丫鬟。
我想,清溪村的石磊,这辈子大概跟我没缘分了。
林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,我却慢慢习惯了厨房里的忙碌。
每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就爬起来,生火、淘米、切菜,手脚从没停过。
林子昂的鸡汤得炖足三个时辰,火候不能断,不然汤就不够鲜。
我得一边盯着火,一边准备夫人的素菜,还要给下人们炒点家常菜。
忙起来时,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,沾湿了衣襟,我都顾不上擦。
翠儿有时候会过来帮我端盘子,她红着眼睛说夫人还是吃不下饭。
“夫人成天念叨着老爷和大少爷,心都碎了,哪还有胃口?”她叹着气对我说。
我听了心里酸酸的,只能低声安慰她:“夫人吉人天相,总会好起来的。”
可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,夫人那样子,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。
林子昂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,阿福说他开始能下床了,但走不了几步。
他整天坐在窗边,盯着院子里的枯树发呆,像是丢了魂。
我偶尔送饭过去,透过门缝看他,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少爷,如今瘦得像根竹竿。
他的腿伤还没好,药味从他屋里飘出来,混着院子里的草药味,呛得人鼻子发酸。
我问阿福:“大少爷这样,真的能好吗?”
阿福摇摇头,低声说:“大夫说,腿能保住就不错了,至于能不能走,得看天意。”
我听了心里一沉,林子昂要是真瘸了,林府的希望就更渺茫了。
这天傍晚,我在厨房忙着洗锅,张七跑进来,神秘兮兮地拉我到角落。
他压低声音说:“听说了吗?永宁侯府来人了,带来了信。”
我一愣,忙问:“什么信?是婚事的事吗?”
张七点点头,脸上带着点幸灾乐祸:“侯府果然不愿让嫡女嫁过来,信里提了庶女的事。”
我倒吸一口凉气,果然被张七猜中了,永宁侯府这是要用庶女替嫁。
“信里怎么说的?大少爷知道了吗?”我急忙追问。
张七耸耸肩:“具体我也不知道,吴叔接了信,脸色难看得像要吃人。”
“估计这事得让夫人和大少爷头疼了,侯府这招,太损了。”
我心里乱糟糟的,替林子昂觉得不值,他那么骄傲的人,怎么受得了这种羞辱?
可转念一想,林府现在这光景,哪还有资格挑三拣四?
晚上,我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,脑子里全是林府的糟心事。
我又想起了石磊,想起他削竹子时低头的模样,心里一阵刺痛。
我在清溪村的日子,虽然苦,但至少有娘在时,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。
如今在林府,我吃得饱,穿得暖,可心却空荡荡的,像少了点什么。
第二天,吴叔把我叫到前厅,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。
他说:“丫头,你的饭做得不错,夫人昨天吃了半碗粥,夸你手艺好。”
我愣了一下,忙摆手:“我哪有那么厉害,都是翠儿教得好。”
吴叔摆摆手,递给我一块碎银子:“拿着吧,算是赏你的。”
我推辞了几句,见吴叔坚持,只好收下,心里却暖洋洋的。
能让夫人吃下半碗粥,我觉得这些天的忙碌总算有了点回报。
可还没等我高兴多久,翠儿跑来告诉我,永宁侯府的信已经送到了林子昂手里。
“大少爷看完信,砸了茶盏,气得一句话都没说。”翠儿咬着唇,眼中满是担忧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,猜到这信肯定没好事,替嫁的事八成是真的。
接下来的几天,林府的气氛更压抑了,连张七都不再哼小调了。
我每天埋头在厨房干活,尽量不去想那些烦心事,可耳朵还是忍不住听墙角。
听说林子昂终于开了口,同意了侯府的安排,但要求见一见那位庶女。
我偷偷松了口气,至少他没彻底放弃,总还有点希望。
可我心里也清楚,林府的路还长着呢,未来的日子,恐怕只会更难。
我攥紧了藏在袖子里的碎银子,暗暗下定决心,不管林府变成什么样,我都要好好干活。
毕竟,我一个十四岁的丫鬟,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
03
林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渐渐适应了厨房的活计。
每天天不亮,我就爬起来,生火、洗菜、炖汤。
林子昂的汤最费工夫,得小火慢炖好几个时辰。
我得盯着火,不能让它灭了,也不能烧得太旺。
有一次,我不小心打翻了半碗鸡汤,急得差点哭出来。
翠儿路过厨房,看我手忙脚乱,笑着说:“青青,别慌,慢慢来。”
她帮我把地上的汤擦干净,还教我怎么熬汤更香。
翠儿是夫人身边的丫鬟,性子温和,待我像姐姐一样。
她告诉我,林子昂以前爱吃红烧肉,可现在伤了身子,只能喝汤。
我听了心里酸酸的,觉得大少爷怪可怜的。
有天晚上,我去送药,看见林子昂靠在床头,脸色苍白。
他皱着眉,额头满是汗,手紧紧攥着被子。
我不敢多看,放下药碗就低头走了。
可那一幕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。
林子昂以前是多风光的人啊,如今却躺在床上,连翻身都费劲。
张七说,林子昂得罪皇帝,可能是因为在朝堂上说了真话。
他不愿巴结权贵,宁可得罪人也要保住自己的原则。
我听了既佩服又替他难过。
这么有才华的人,怎么就落得这下场?
那天夜里,我又梦见了石磊。
梦里他在溪边削竹子,我站在对岸喊他。
他抬起头,冲我笑了笑,可没说话。
我醒来时,眼角有点湿。
我摸出枕头底下的旧发簪,那是石磊小时候送我的。
簪子已经旧了,可我一直舍不得扔。
看着它,我想起了清溪村的溪水,还有石磊安静的笑。
可如今,我是林府的丫鬟,石磊远在千里之外。
我叹了口气,把簪子塞回枕头底下,继续去厨房干活。
林府的日子不好过,可我得活下去。
为了林府,也为了自己。
过了半个月,二少爷林子墨回来了。
那天我刚择完菜,得了空,在后院洗衣服。
突然听到前院马儿嘶鸣,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林府自从出事后,一直死气沉沉的。
这突如其来的动静,吓得我心跳加速。
我暗自嘀咕,不会是有人来抄家了吧?
鼓起勇气出去看,差点撞上一个人。
那人风尘仆仆,步子急得像一阵风,直奔夫人院子。
我只瞥见他衣角一闪,没看清模样。
他身后跟着管家吴叔,跑得气喘吁吁。
吴叔路过我,停了一下,说:“青青,快去给二少爷烧热水!”
他眼里闪着久违的光彩,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我愣愣地应了声,细想他的话——二少爷?
夫人院子里传来一声带哭腔的喊:“娘,儿子回来晚了!”
我心里跟着一颤,眼眶有点酸。
二少爷回来了,林府终于人齐了。
我赶紧去烧热水,还多加了两道菜。
我想,夫人肯定不希望二少爷知道家里现在吃得差。
林子墨回来,府里总算有了点生气。
吴叔管家多年,看着林子墨长大,这几天交代事时,脸上居然有了笑。
林子墨一回来,就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。
他给夫人和林子昂诊脉,还亲自买了人参回来炖汤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,看他忙前忙后,觉得他真是个孝顺的人。
林子墨回来,不能没人伺候,张七被调到他院子里。
洒扫的活,吴叔说各院自己打扫。
前厅和回廊的活,落到了我头上。
我终于能走出小厨房,到府里其他地方看看。
林府的宅子修得特别精致,园子里假山流水,雅致得很。
听说是当年太子看重林子昂,特意请名家设计的。
可我没时间细看,只能匆匆扫一眼。
我手里的活本来就多,现在又加了洒扫,几乎没空闲。
回廊没什么人气,扫的也就是些落叶。
幸好还没入秋,我早晚各扫一次就够了。
一天晚上,我收拾完厨房,碗筷晾在架子上。
我照例拿扫帚去扫前厅,走到回廊,听到一阵箫声。
那声音在月光下流淌,带着说不出的孤单。
我站在回廊上,远远看去,北边是夫人的院子。
风吹过,能看见花枝轻轻晃动。
南边是大少爷的院子,藏在一片绿竹后。
再往南是二少爷的院子,只能看到一角青瓦。
箫声从南边传来,也不知是林子昂还是林子墨吹的。
我听着入了迷,抱着扫帚靠在柱子上。
最后怎么回的屋,都记不清了。
梦里仿佛还有那悠悠的曲调。
后来再去扫院子,却没再听到箫声。
那一夜的灯火摇曳,好像只是我的幻觉。
我忍不住问张七:“那天晚上的箫声,是谁吹的?”
张七挠挠头,说:“可能是二少爷吧,他爱吹箫。”
“不过大少爷也会,兴许是他心情不好,吹着散心。”
我点点头,心想,林府的人,心里都藏着事吧。
04
二少爷回来第五天,夫人来厨房了。
她站在灶前,熬了一碗清凉的绿豆汤。
还捣碎了去年的干桂花,像是要做桂花糕。
这是夫人第一次来厨房,身边没带翠儿。
她不说话,我也不敢开口。
我只悄悄抽出几根烧得太旺的柴,把火调小。
抬头一看,夫人脸上滑下两行泪。
她哭得无声无息,身子绷得紧紧的。
我心里一酸,不知道她有多难过。
我第一天来林府时,去夫人院子里认过脸。
那时候她端庄温柔,像个大家闺秀。
现在不过半个月,她头发白了不少,人也瘦了一圈。
我知道,夫人是来给二少爷做吃的。
张七说,夫人要把二少爷送回书院,明天就走。
林府现在这样,二少爷回来也帮不上忙。
林府想翻身,朝堂上得有人,二少爷得继续读书考功名。
这绿豆汤和桂花糕,准是二少爷小时候爱吃的。
夫人一边搅拌面糊,一边低声说:“子墨小时候,最爱吃这个。”
我壮着胆子说:“夫人,我家乡的面条也好吃,要不要试试?”
夫人愣了一下,笑了笑,说:“好,改天你做给我尝尝。”
我心里一暖,觉得夫人真是个好人。
我从怀里掏出手帕,叠整齐放在她手边。
然后轻轻关上门,蹲在墙角抱膝坐下。
夫人这样子,让我想起了我娘。
小时候,娘也会给我煮面条。
娘走后,我学会了做饭,在后娘手下讨生活。
现在又来林府谋生。
林府再落魄,也是个家。
可我,已经没家了。
夫人在厨房里哭,我在外面发呆。
天边的夕阳红得像血。
过了一会儿,我拍干净衣服上的灰,推门进去。
夫人已经收拾好情绪,正在整理面盆。
她眼角有点红,但脸上已经看不出泪痕。
我问:“夫人,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?”
夫人说:“舀一碗水来。”
她一边忙,一边问我:“青青,你当时为什么留下来?”
府里留下的几个人,她只对我不熟。
我老实说:“除了林府,我没地方去。”
夫人叹了口气,说:“现在的林府,也不是什么好去处。”
张七也说过这话。
可对我来说,哪不用干活?
林府有屋顶遮雨,有饭吃,还有月银。
这已经是最好的日子了。
夫人看着我,笑了笑,说:“你是个好姑娘,帮我照顾好子昂。”
我点点头,心里沉甸甸的。
一个月后,南州来了一封信。
夫人看完信,当场晕了过去。
张七跑出去请大夫,我守着灶,熬了一锅小米粥。
我怕夫人醒来饿了,得吃点东西。
后来听吴叔说,信不是林老爷写的,是周大爷写的。
信里说,林老爷在去南州的路上得了病。
他们在路上歇了两天,病情没好转。
林老爷怕误了上任的日子,硬撑着赶路。
到了南州,他咳得下不了床。
第二天,夫人醒来,决定要去南州陪林老爷。
吴叔劝了半天也没劝住。
最后惊动了林子昂。
我来林府这么久,第一次好好看到他。
上次他被抬回来,血肉模糊,我只远远瞥了一眼。
之后一个月,他一直在屋里养伤,没踏出一步。
现在,他穿着一件素白长袍,坐在轮椅上。
阿福推着他,进了夫人院子。
张七说过林子昂的风光,却没说过他的模样。
现在见了,我差点看呆了。
林子昂生得太好看了。
他皮肤很白,嘴唇也淡,穿着白袍,像庙里的玉雕菩萨。
可他眼下有淡淡的青黑,像是好久没睡好。
他进夫人院子没多久,翠儿出来拿我手里的粥。
夫人终于肯吃东西了。
趁夫人吃饭的空当,林子昂让张七拿着信去药铺。
他让张七按信里的症状抓药,再买些保命的药丸。
林子昂说,既然劝不住夫人,那就做好准备。
夫人要去南州,身边得带人。
翠儿是夫人的人,肯定要跟去。
吴叔经验老到,也被林子昂点名随行。
最后,他还点了张七,说他年轻力壮,能帮忙。
夫人本来不想带张七。
林子昂还带着伤,家里这光景,夫人不想带太多人。
再说,南州还有周大爷在。
可林子昂只是轻轻挑眉,夫人就不说话了。
我站在院子外,听着他们的对话,心里有点酸。
林子昂虽然病弱,可还是为家里操心。
那天晚上,我听见翠儿和吴叔在院子里说话。
翠儿说,林老爷的病很重,怕是撑不了多久。
我吓了一跳,手里的菜刀差点掉地上。
第二天,夫人开始收拾行囊。
我帮她整理衣服,看到她眼眶红红的。
她把一枚玉佩塞给我,说:“青青,留个念想。”
我攥着玉佩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我还准备了些干粮和蜜饯,用油纸包好。
夫人问我是什么,我说:“是路上吃的点心和防晕船的蜜饯。”
第二天一早,我起来熬粥。
夫人他们吃完粥就出发,车马早就备好了。
临走时,夫人又哭了。
她用帕子捂着脸,眼泪止不住。
风吹得冷冷的,像一下子入了秋。
我红着眼睛,把包裹递给翠儿。
林子昂坐在轮椅上,脸色平静。
他穿得单薄,衣袍被风吹得飘起来。
他的背瘦得厉害,肩胛骨凸出来,像要飞走似的。
他开口,声音很沙哑:“时辰差不多了。”
05
就这样,夫人带着吴叔、翠儿和张七走了。
偌大的林府,只剩我、林子昂和阿福三个人。
府里空得吓人,我回到厨房收拾碗筷。
腰又开始酸了,可能是昨晚熬粥没睡好。
我揉了揉腰,决定今晚早点休息。
张七走前教我劈柴的法子,说这样省力。
我试了试,果然轻松不少。
可劈完柴,厨房里安静得只剩锅里水咕嘟的声音。
远处传来几声犬吠,我突然想起娘走的那天。
那天也是这么安静,我一个人坐在灶前哭。
现在,我又是一个人了。
阿福掀帘子进来,说林子昂有话交代。
他说,家里只剩三个人,往后一起吃饭,不用单独给林子昂做。
这对我来说是好事,少了不少活。
可总觉得有点不合规矩。
中午,我炒了四道菜,端到林子昂的院子。
这是我第一次进他的院子。
以前送饭,都是到门口,阿福就拿走了。
林子昂没坐轮椅,阿福扶着他,在院子里练习走路。
他走得不好,嘴唇抿得紧紧的,额头满是汗。
我不敢打扰,低头把菜摆桌上。
我暗自后悔没用食盒,菜都凉了。
正想着,就听见阿福一声惊呼。
我转头一看,林子昂膝盖一软,摔倒在地。
阿福被他带倒,两个人摔得狼狈。
旁边的花架被撞翻,花瓶砸下来,碎了一地。
我吓得愣住,下意识跑过去。
林子昂喊:“小心!”
我低头一看,地上满是碎瓷片。
阿福的额头被划了个小口子,血流到下巴。
林子昂看着没事,但站不起来。
我跟阿福一起把他架起来。
我帮他抖了抖衣服,确认没碎片,才让阿福扶他坐下。
阿福的血还在流,林子昂让他去处理伤口。
我拿扫帚清理地上的碎瓷片。
阳光照在瓷片上,闪着光,我一晃眼,看见裙子上也有血。
我以为是阿福的血,可他的血没沾到我身上。
我低头检查,没找到伤口。
碍于林子昂在,我不好掀裙子看。
林子昂看出我的不对,问:“你在找什么?”
我把裙子上的血迹给他看,说:“我好像受伤了,可奇怪,哪儿都不痛。”
他看着我,耳尖突然红了。
他咳了一声,问:“你今年多大?”
“十四。”
小腹突然一紧,裙子上又晕开一抹红。
空气安静得吓人。
林子昂压低声音说:“你,可能是来月事了。”
我脑子嗡嗡响,又羞又慌,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
我说:“那……怎么办?”
林子昂愣住了,结结巴巴地说:“你娘没教过你吗?”
“我娘早就没了,没来得及教。”
后娘提过月事,可她只想着让我去王老爷家。
她没教我怎么处理,也没让我准备月事带。
我从没想过要备这个。
夫人和翠儿都走了,府里没一个女人。
小腹越来越痛,像坠了块石头。
十四年来,我从没这么无助过。
我咬着唇,眼眶红了,想先回去换衣服。
眼前一黑,一件外袍盖在我身上。
是林子昂的外袍,还带着他的体温。
他别过脸,说:“你先穿上。”
阿福处理好伤口回来,看到这场面,傻了眼。
他揉了揉眼睛,喃喃道:“我这是伤到脑子了?”
林子昂咳得脸都红了,挥手让他退下。
阿福走路都飘了,像在做梦。
林子昂恢复了镇定,说:“推我去厨房。”
我问:“去厨房干嘛?”
“找些草木灰,再去翠儿的房间。”
我红着脸,低声问:“找什么?”
他平静地说:“翠儿应该留了月事带,你照着做。”
我脸烫得能煎鸡蛋,推着轮椅的手紧了又紧。
我说:“哦。”
到了厨房,我找到草木灰,又去了翠儿的房间。
果然找到几条月事带,我照着样子做了起来。
林子昂在院子里等我,远远地问:“弄好了吗?”
我小声说:“弄好了,谢谢大少爷。”
他没说话,只点了点头。
回厨房的路上,阿福悄悄拉住我,问:“刚才怎么回事?”
我红着脸解释:“我来月事了,大少爷帮我出主意。”
阿福哈哈一笑,说:“大少爷脸都红了,吓死我了!”
我瞪了他一眼,心想,这事可别传出去。
06
从前林府风光无限,仆人多得数不过来,夜里灯火通明。
现在却冷清得像座空宅。
夜里我睡不着,翻来覆去。
平时翠儿睡在离我不远的厢房。
更远处的房间住着吴叔和张七。
可现在夫人带着他们走了,长长的厢房只剩我一个人。
阿福一直住在大少爷院子,方便照顾林子昂。
窗外的风呼呼地吹,像野狼在嚎。
我突然想起张七逗我时讲的鬼故事。
他说大宅子里常有怪事,井里泡着死尸,半夜能听见女鬼哭。
林府的厢房雕梁画栋,白天看还好。
可现在烛火灭了,我一个人,吓得头皮发麻。
我试着点灯,壮胆查看房间。
可窗外影子晃动,像有人在走,我更害怕了。
我裹紧被子,越怕越想上茅房。
我压着肚子,硬是熬到睡着。
早上洗脸时,我看着水里的倒影。
脸色苍白,眼圈发黑,像张七说的女鬼。
我安慰自己:“青青,别怕,不过是风声。”
只做三个人的饭,加上洒扫,活计不算重。
我干完活,把林子昂借我的外袍洗得干干净净。
然后靠在柴堆上,闭上眼睛休息。
初来月事,身上酸痛得厉害。
从夫人晕倒那晚起,我三天没睡好。
我太累了,只想歇一会儿。
可一睁眼,夕阳的余晖从窗子洒进来。
空气里飘着金色的尘埃。
我吓得跳起来,天都快黑了!
现在才烧火,肯定误了林子昂的饭。
如果因为我让主子饿肚子,我可怎么办?
我慌得不知是先请罪还是先煮饭。
最后我先烧上水,提着裙子跑去林子昂的院子。
我跑得太急,半路摔了一跤,裙子沾了泥。
到了院子,我低头说:“大少爷,奴婢睡过了,误了饭点。”
林子昂正翻着一本书,闻言抬头。
他没生气,淡淡地说:“既然晚了,就别炒菜,下面条吧。”
主子这么宽容,我却出错,羞得脸都红了。
我低头退下,不敢看他的表情。
面条我从小就会做,帮我娘在摊子上练熟了。
可来了林府,还没做过。
我回忆娘教我的法子,擀面、切条、下锅。
三碗面很快端上来,阿福吃得快,稀里哗啦就吃完了。
林子昂只吃了一口,就放下筷子,皱着眉。
我心跳到嗓子眼,问:“是不是不合您口味?”
他问:“你是清溪镇白水村的吧?”
我愣了,说:“是,少爷怎么知道?”
林子昂眼神柔和,像在回忆什么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随父亲进京,在你娘的摊子上吃过面。”
我吃了一惊,没想到有这缘分。
可一想到娘已经不在了,我心里酸酸的。
林老爷也在南州,生死未卜。
这碗面还是那味道,可人已经不在了。
林子昂大概也有些感伤,换了话题。
他说:“你做事挺踏实,今天怎么睡过头了?”
我不敢撒谎,说:“昨晚害怕,没睡好,中午想眯一会儿,没想到睡过头。”
他问:“怕什么?”
我说:“这宅子太大,我一个人睡,怕黑。”
林子昂点点头,说:“你年纪还小,怕黑也正常。”
我听出他话里有送我走的意思,急了。
我说:“奴婢不小,能干活!今晚我不怕了,明天绝不误事!”
林子昂笑了,说:“别慌,怕黑谁都有。”
“我院子里有空房,你吃完饭收拾一下,搬过来住吧。”
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,连声道谢。
我说:“锅里还有汤,我去盛来。”
晚上风里带着槐花的香,我心情好,不怕黑了。
阿福在后面喊:“青青,还有面吗?没吃饱!”
我笑着回头,挥手说:“管够!”
搬到新房间,我发现桌上有一本旧书。
封面上写着林子昂的名字,字迹工整。
我好奇地翻了几页,都是诗词。
我猜,这是他年轻时写的吧。
夏天雨水多,院子里的草长得疯快。
没人打理,草木遮住了阳光,地上生了青苔。
我们村里空屋子就是这样荒掉的。
林府这么好的宅子,荒了多可惜。
我请示林子昂,开始整理院子里的花木。
院子里有棵老槐花树,开得特别好。
我舍不得扫树下的落花,喜欢爬上去玩。
我折一片叶子,卷起来吹,阳光洒在花枝间。
地上落着斑驳的光点,这是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。
可也有难过的时候。
每次从树上看到林子昂练习走路,我心里就发闷。
他走得很吃力,右腿像是使不上劲。
阿福已经不扶他了,他拄着两把订做的木拐。
他每迈一步,额头就渗出汗。
我问阿福:“大少爷的腿,什么时候能好?”
阿福叹气,说:“能走路就不错了。”
每天中午,郎中来给林子昂施针。
可过了这么多天,好像没什么效果。
有一次,我送郎中出去,忍不住问:“少爷的腿还能好吗?”
郎中说:“能保住命,已经是万幸。”
他说,廷杖有两种,一种三十下能打死人。
另一种五十下能留口气,林子昂挨的就是这种。
行刑的人手下留情,他才捡回一条命。
我听得心里发酸。
林子昂那么有才华的人,怎么落得这下场?
我熬药时,偷偷加了点家乡的草药偏方。
希望能对他有点用。
07
那天夜里下了大雨,雷声轰隆。
雨点从窗缝打进来,我被惊醒。
我去关窗,听到雨声里夹着断续的箫声。
那声音低沉,像在哭。
我突然想起上次听到的箫声。
原来是林子昂吹的。
今晚的箫声断断续续,像喘不过气。
我心一紧,穿上鞋就往他院子跑。
雨下得太大,树被吹得东倒西歪。
我跑得跌跌撞撞,衣服湿透了。
阿福住旁边的耳房,门关着,估计睡了。
林子昂的门也关着,我犹豫要不要敲。
深夜闯主子房间,太没规矩了。
可我担心他,轻轻敲了敲门。
没人应,我又用力敲了一下,说:“大少爷,您没事吧?”
还是没动静,我正想走,门突然开了。
我正趴在门上听,门一开,我摔了进去。
林子昂一把扶住我,身上冷得像冰。
他坐在轮椅上,脸色白得吓人。
他问:“有什么事?”
我说:“我听到箫声,怕您不好。”
他声音干涩,说:“没事。”
可他明明冷得发抖,哪叫没事?
我说:“您等着,我去拿东西!”
我冒雨跑回厨房,生火烧水,灌了两个汤婆子。
我还抓了一瓶白酒,想给他暖身。
跑回去时,我才发现廊上的风灯都灭了。
我竟然忘了怕黑。
林子昂站在门口,拄着拐,像是等急了。
看到我,他松了一口气。
我打了自己一耳光,怪自己跑太快,没听他喊什么。
我把汤婆子塞给他,扶他进屋。
关上门,风雨被挡在外面。
屋里点着油灯,暖黄的光让人安心。
可林子昂肩膀湿了一片,我更担心了。
我说:“您不会发烧吧?我去煮姜汤!”
他没说话,从柜子里拿出一套衣服。
我以为他要换衣服,转过身去。
他拍拍我肩,说:“换上。”
竟然是给我的衣服。
我不想再穿他的衣服,可看到他嘴唇咬出血了。
我不敢犟,躲到屏风后换好。
我又拿了套衣服,帮他换上,扶他趴到床上。
我把屋里能盖的东西都盖到他身上。
可他还是冷得像冰,汤婆子不够用。
我问:“大少爷,您冷吗?”
他说:“还好。”
可他的嘴唇都发青了,哪有半点还好?
我端起白酒,想给他喝,又想起他刚喝了药。
我只好放下酒,低声说:“大少爷,别怪我。”
他一脸茫然,问:“怪你什么?”
我钻进被子,把手伸到他腿上。
我隔着衣服,从他腿开始揉,慢慢往上.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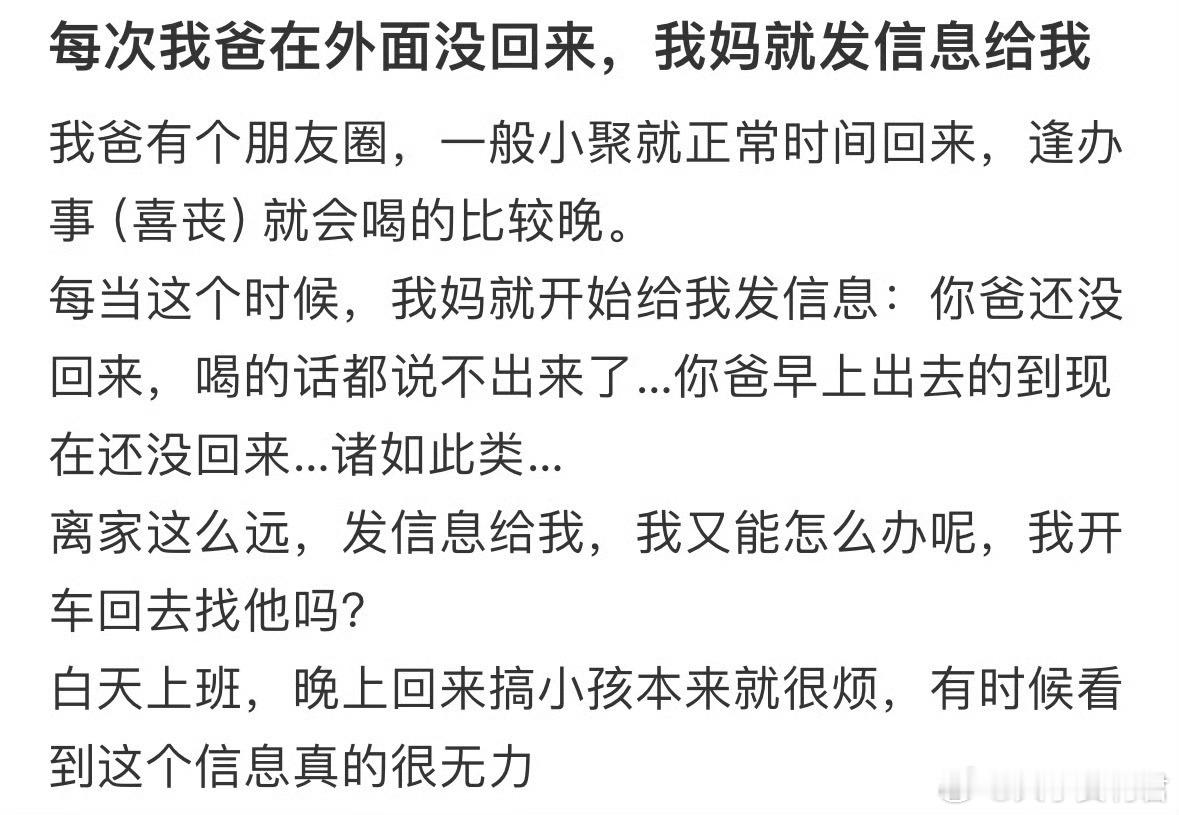

评论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