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语》里有一条记录,孔子发火了,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愤怒!

季氏富于周公,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: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第十一》)
彼时,孔子的弟子冉求(也称冉有)给鲁国最有权势的季氏做家臣。
季氏当权,气焰正盛,冉求不仅没有劝阻季氏,反而帮他继续敛财。
这让孔子很愤怒,就说了这句话:
“冉求不算是我的弟子,大家可以大张旗鼓去声讨他。”
其实,在孔门中,冉求是孔子很器重的学生。
德行: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:宰我、子贡。政事:冉有、季路。文学:子游、子夏。(《论语·先进第十一》)
孔子弟子三千,贤者七十二,其中,冉有和子路就是“政事科”的代表。

在《论语》里,还有一段记录:
季康子问: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?”
子曰:“由也果,于从政乎何有?”
曰: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?”
曰:“赐也达,于从政乎何有?”
曰: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?”
曰:“求也艺,于从政乎何有?” (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)
季康子(季氏)分别询问了孔子的三位弟子(子路,子贡与冉有):他们的从政能力如何?
孔子非常精准概括了三人的特点:
子路“果”,决断力强(适合处理危机或需要魄力的政务)。
子贡“达”,通达权变(适合处理外交事务、协调各种关系)。
冉求“艺”,多才多艺,精通礼乐射御等技能(适合处理日常行政事务)。
三人这样的水平,处理政事有啥困难呢?
因为季康子僭越礼制(曾经搞过“八佾舞于庭”),孔子在点评弟子的时候,只回应才能,未提德能,暗含对季氏用人只侧重才能的警示。

从《论语》另外的记录里,也能看出孔子对冉有非常看重。
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“庶矣哉!”冉有曰:“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”曰:“富之。”曰:“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”曰:“教之。” (《论语·子路第十三》)
孔子去卫国,冉有以弟子的身份为他驾车,见到人群熙攘,孔子感慨:人真多啊。
冉有就问:人口稠密,接下来咋整呢?
孔子当机对冉有阐述了“庶-富-教”的治国理念。
孔子对每个学生的教诲是不同的,根据每个学生的特色而指点提策。
对于冉有,孔子能够给他讲述为政治国理念,可见很是认可冉有的为政才能。

《论语》里还有一段记录:
子路问:“闻斯行诸?”
子曰:“有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?”
冉有问:“闻斯行诸?”
子曰:“闻斯行之。”
公西华曰:“由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‘有父兄在’;求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,敢问。”
子曰:“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” (《论语·先进第十一》)
同样是询问:“听到了就去做吗?”
对于性格急躁的子路,孔子就回答:你还有父兄在,急个啥?听听他们的意见啊。
而对于性格有些畏缩的冉有,孔子就鼓励:啥也别说了,撸起袖子加油干!

子路和冉有同样做了季氏家臣,《论语》有这样一段记录:
季氏将伐颛臾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。
冉有曰:“夫子欲之,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
孔子曰:“求!周任有言曰:‘陈力就列,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则将焉用彼相矣?且尔言过矣,虎兕出于柙,龟玉毁于椟中,是谁之过与?”
冉有曰:“今夫颛臾,固而近于费。今不取,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
孔子曰:“求!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吾恐季孙之忧,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。(《论语·季氏第十六》)
季氏准备攻打附庸小国颛臾,冉求和子路就来找孔子。
冉有张口就甩锅:“是季氏想打,我们俩不想打。”
孔子哪能看不出这些小心思,他厉声斥责:在其位,谋其政,不行就该辞职。
冉有又找借口说:颛臾这地方很重要,如果不打,迟早是个威胁。
孔子一下就指出他是在为季氏的贪欲找借口(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)。

接着孔子阐述了“均、和、安”的政治理念,并预言季氏的忧患不在外部而在内部(而在萧墙之内也)。
在这个对话里,孔子两次都是直呼冉有的名字:求!
你想想你爸妈喊你全名的时候,就能想到当时是什么情形了。
有人说,孔子对冉求的态度是矛盾的。
其实,回到老师和学生的角色上,我们能发现更多人性的秘密。
同时也会发现:
师之用心,何其良苦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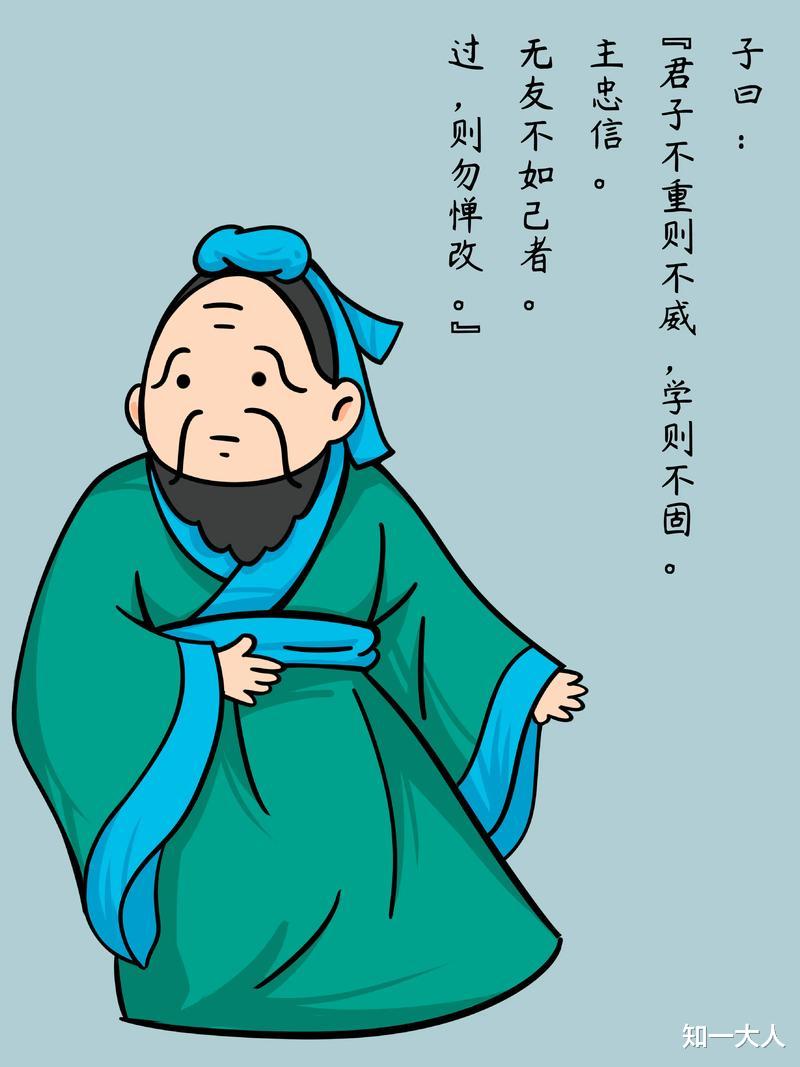
孔子怒称冉有“非吾徒也”,是在棒喝,也是断冉有心里的退路。
冉有做季氏的家臣,孔子多次提醒他:要遵循本心,劝谏行善。
但冉有没有这样做,而且在面对孔子时会甩锅:是季氏要这么做,跟我没关系!
潜台词是:我很无力,我也没办法,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
在这样的情形里,作为老师的孔子,看穿了冉有的行为模式,能够看到他的行为在循环往复。
而且,苦不自知。
人背离自己的心,是最苦的。
这样,我们就能理解,孔子的厉声呵斥,其实不是不要冉有这个弟子了,而是充满了怜惜之意。
评论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