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潮汕地区,可以说1991年是一道深刻的分水岭。这一年汕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,而且在此之后,"三分天下"的格局重塑了粤东的政治经济版图。这场改变百万人生计的区划调整,并非偶然的行政切割,而是特区发展诉求与体制困境碰撞的必然结果,其背后的博弈与抉择,至今仍影响着潮汕三市的发展轨迹。
1991年之前的汕头市,是名副其实的潮汕核心。其管辖范围北至饶平山区,南抵南澳海岛,西达揭西丘陵,东接澄海平原,囊括了安平、东平、公园、金沙、达濠、郊区6个市辖区,揭阳、饶平、澄海、南澳、朝阳、普宁、揭西8个县,以及县级潮州市和汕头经济特区,陆域总面积达10346平方公里。
在这片土地上,潮汕话互通、民俗同源、商脉相连,大汕头不仅是行政概念,更是根深蒂固的地域认同。 然而,光鲜的大一统表象下,体制性隐忧早已暗流涌动。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汕头经济特区与汕头市的关系上。

同时期的深圳、厦门、珠海均实现了特区与地级市的"一体化"管理,即特区政府便是市政府,政策覆盖全域;而汕头经济特区虽隶属于汕头市,却拥有独立的领导管理机构,两者仅明确了行政级别对等,权责划分、政策衔接等核心问题始终未能理顺。
这种"一市两制"的格局,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困扰。同一座城市里,特区内企业能享受税收减免、外资审批简化等政策红利,特区外的企业却只能望洋兴叹;甚至连居民的教育、医疗资源分配,也因"特区内外"的身份差异而存在隐性差距。
更关键的是,经过1980年代两次扩围后,汕头经济特区面积仅为52.6平方公里,在四大特区中垫底,尽管当时的汕头领导层对此有着清醒认识,要释放特区活力,必须打破空间桎梏;而要扩大特区范围,就不得不直面体制顽疾,所以一场关乎潮汕未来的调整,已在时代浪潮中悄然酝酿。

到了1990年代初,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,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亟需通过空间拓展转化为发展动能。汕头特区的扩围诉求,得到了广东省乃至中央的关注,但一条不成文的政策红线却横亘在前,经济特区最多只能管辖一个县。,而这一限制成为引爆潮汕区划调整的导火索。
1991年1月19日,来自上级的明确答复传至汕头,特区可扩大至整个市区,但额外管辖的县域最多只能增加一个。这意味着,扩围绝非简单的空间扩容,而是必然涉及行政区划的系统性重构,就是说原汕头市下辖8县1市,若特区仅带一县,其余近三四十倍于市区的县域如何安置?特区与剩余区域的行政关系如何界定?这些问题如连环锁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彼时,汕头领导层面临着四大棘手难题。
其一,若特区仅小范围扩大,无法突破发展瓶颈,意义甚微;若扩大至整个市区,又必然与原汕头市的行政边界重叠,两者的管理关系必须彻底调整。
其二,若参照厦门、珠海的先例将特区扩至全汕头市,则需管辖8县1市,远超"带一县"的惯例,极难获得上级认可。
其三,即便获准带一县,该选择哪一县?是经济活跃的普宁,还是地理相近的朝阳,或是历史悠久的揭阳?
其四,剩余县域若脱离汕头管辖,如何划分才能兼顾历史渊源与发展需求?

在1991年4月6日,《关于扩大汕头经济特区范围的批复》正式下达,这份文件成为潮汕分治的"催化剂"。批复明确同意特区扩至汕头市区,总面积达234平方公里,原达濠区的棉花村、马教街道等区域需重新规划;但对特区能否继续管辖原8县1市,文件只字未提,反而强调"现行汕头市的行政区划需作出相应调整"。
这一表述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潮汕分拆已势在必行,所以在50多天后的5月28日,《汕头日报》与《汕头特区报》在头版头条同步刊发批复内容,消息迅速传遍潮汕大地。市民们既为特区扩围带来的发展机遇振奋,又对即将到来的区划调整满怀忐忑;官场则暗流涌动,能否留在特区范围内任职,成为各级官员关注的焦点。
当年9月14日,汕头市区率先完成调整,6个区整合为4个区,机构精简与干部调配顺利落地,为后续的全域分拆铺平了道路。但原汕头市下辖的8县1市如何安置,仍是摆在领导层面前的"大考题"。
最初,汕头领导层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。

方案一为"一分为一",即特区扩围后,原8县1市的管辖范围保持不变,继续由汕头市统筹。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—。此前上级已对类似提议表达过否定态度,且与"特区带一县"的原则相悖,缺乏实操性。
方案二为"一分为二",将特区设为一个地级市,剩余7县1市(除南澳县)合并为另一个地级市,拟以县级潮州市为驻地。 "一分为二"的方案看似合理,却经不起现实推敲。从地理上看,剩余县域从饶平到惠来跨度超100公里,从揭西到澄海也有百余公里,行政指令的传达与执行极为不便。
而且更突出的是交通问题,如果惠来居民若要前往潮州办事,需先绕道汕头市区,再行驶50多公里才能抵达,往返耗时耗力。此外,县级潮州市虽已是广东省仅存的非地级市,经济独立核算,但行政级别低于汕头半级,难以承担统筹全域的重任。

经过反复论证,"一分为二"方案因"管理成本过高、协同性不足"被否决。 排除了两种可能性后,"一分为三"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。汕头作为特区所在地,潮州凭借历史地位与县级建制基础,自然成为两个地级市的首选。而第三个地级市的选址,引发了揭阳、普宁、朝阳三县的激烈角逐。
为保证考察的公正性,汕头领导层组建了由林、老、曾三人组成的考察组,并定下"约法三章",仅允许三人家参与考察;到达考察点后"只听不说",不发表任何意见;汇报仅限各县一二把手参与,其他人不得在场。
然而,当考察组抵达第一站揭阳县时,"约法三章"便被打破——全县五套班子倾巢而出,主要领导亲自到场迎接,场面隆重而热烈。 揭阳县强调自身历史悠久、拥有榕江出海港口、经济总量领先;普宁县则聚焦商品流通优势,其颇具规模的专业市场成为汇报重点。

朝阳县则突出与汕头市区仅10多公里的地理优势,宣称能快速承接特区辐射。在朝阳县的汇报会上,当听到部分财政数据时,考察组中有人随口追问"难道有这么多",这句打破"不表态"原则的话,一度被解读为领导层对朝阳建市的否定。
最终,考察组虽未当场表态,但心中已有了清晰判断。 从结果来看,揭阳的胜出绝非偶然。相较于朝阳,其与汕头市区距离适中,避免了"中心城区间距过近"的行政禁忌;相较于普宁,其优势更为显著:历史上曾为郡治所在地,文化底蕴深厚;拥有榕江直通汕头港的天然良港,交通优势突出;地域面积更大,经济基础更扎实。
此外,揭阳与揭西县历史联系紧密,而揭西作为山区县,距汕头、潮州较远,归入新设立的揭阳市更为合理。也有观点认为,朝阳与普宁的"鹬蚌相争",客观上为揭阳的"渔翁得利"创造了条件。

1991年底,原汕头市被拆分为汕头、潮州、揭阳三个地级市。汕头市保留特区建制,管辖调整后的4个市区及南澳县;潮州市升格为地级市,管辖原潮州市区及饶平县;揭阳市新设为地级市,管辖揭阳、普宁、揭西、惠来四地。在这场调整中,仅有饶平县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,其余区域均接受了这一格局。
至此,延续数十年的"大汕头"时代落幕,潮汕地区进入"三市并立"的新纪元。这一调整在当时展现出显著的积极意义,汕头特区得以摆脱庞大县域的拖累,专注于外向型经济发展;潮州凭借文化优势深耕旅游与特色产业;揭阳则依托港口资源发力重工业与商贸。三市各自的发展定位更加清晰,行政效率得到提升,特区政策的红利也通过三市的联动逐步扩散至整个潮汕地区。
然而,分治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原本统一的市场被行政区划分割,产业同质化竞争、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逐渐显现;潮汕文化的整体性虽未被割裂,但三市在文化品牌打造、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协同不足,未能形成合力;更令人唏嘘的是,曾经"同饮韩江水"的地域认同感,在行政边界的阻隔下逐渐淡化。

如今,三十余年过去,回望1991年的那场分治,历史评价已然多元。当年的支持者认为,分治释放了三市的发展活力,避免了"大而不强"的困境,揭阳的崛起、潮州的转型、汕头特区的升级,都印证了调整的必要性;反对者则感慨,若能保持行政统一,潮汕或许能形成更强的区域竞争力,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。
但无论评价如何,一个事实无法改变:1991年注定是潮汕历史上的"关键之年"。这场因特区扩围引发的区划调整,既是改革开放进程中行政体制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,也是地域发展与文化认同碰撞的生动注脚。正如潮汕人常说的"世事如棋",当年的决策者或许未能完全预见今日的格局,但他们的抉择,确实塑造了当代潮汕的基本面貌。
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,汕头、潮州、揭阳正逐步重拾"潮汕一家亲"的共识,在交通互联、产业协同、文化共建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。或许,当年的"三分"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,而未来的"融合",才是对潮汕文化根脉的最好传承。1991年的故事,终究会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,见证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生命力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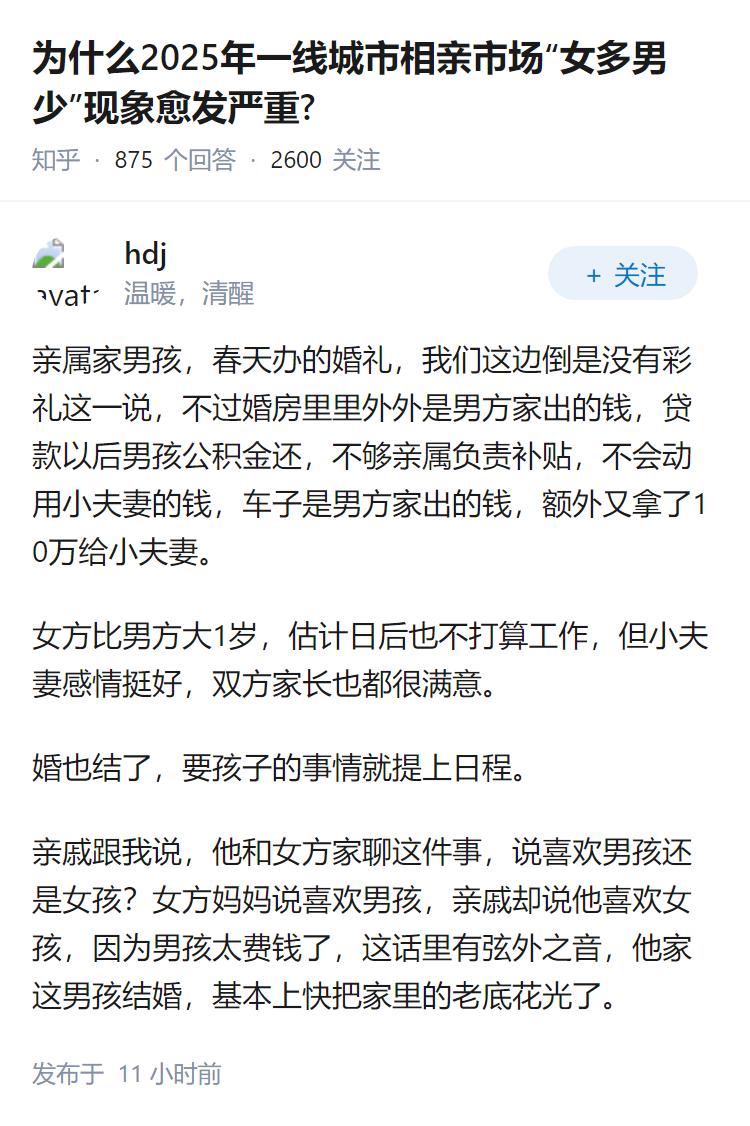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