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棍二叔才 56 岁,上吊去世了,侄子都不想管,草草拉到火葬场,回来就埋了,从发现死亡到下葬只用了半天时间。 半年后村后荒坡修路,施工队的铁铲碰到个硬东西,挖出来一看是个没刻字的骨灰坛。队长捏着坛沿上的土疙瘩给大明打电话时,他正在县城工地捆钢筋,手机贴在耳朵上,听着听着就蹲了下去,钢筋砸在脚边溅起的泥点,糊了满裤腿。 小明是开着小货车赶来的,车斗里还堆着没送完的蔬菜。两人蹲在被挖开的土坑边,看着坛身磨出的毛边,谁都没说话。这坑是半年前他们亲手挖的,铁锹下去时土块还带着冻碴,埋完连脚都没跺实就走了——那天下午的风刮得紧,荒草在身后追着咬裤脚,像有人在骂“没良心”。 发现二叔出事的是隔壁张婶。那天早上七点多,她攥着布袋去喊二叔赶集,拍了十几下门板没应声,那扇掉漆的木门却留着道缝。张婶后来跟人说,她是被风推着进去的,一抬头就看见房梁上悬着的身影,蓝布褂子在穿堂风里晃,像片干硬的叶子。她尖叫着往门外跑,鞋都跑掉了一只,布鞋在泥路上滚出老远。 村里老人打电话时,大明正扛着水泥往三楼爬。电话里说“你二叔没了”,他手一松,水泥袋砸在楼梯上,灰扬了满脸。他抹了把脸跟工头请假,工头骂骂咧咧扣了半天工钱,他没吭声——心里想着二十年前,二叔背着他过村前小河,河水漫到二叔膝盖,他趴在背上数着二叔脖子上的汗珠,一颗一颗滚进衣领里。 小明接到电话时,正跟卖菜的大婶为一毛钱争得面红耳赤。手机在兜里震,他夹着电话说“马上回”,挂了却蹲下来把烂菜叶挑干净才开车。车过村口桥时,他瞟了眼桥洞——小时候二叔总在那儿教他打弹弓,石子打中水面的涟漪,像二叔笑起来的皱纹。 两人中午凑到二叔家,屋里还飘着酒气。几个老人坐在门槛上叹气,说“好歹停一天,请个先生看看”。大明踢了踢墙角的空酒瓶,瓶身滚到桌边,撞翻了二叔没喝完的半杯酒。“停啥?”他声音有点哑,“他这辈子最烦热闹,咱别折腾他了。”小明低头扯了扯裹尸的白布,布角蹭过二叔枯瘦的手腕,像摸到了小时候二叔塞给他的糖纸,糙糙的,却甜得扎心。 火葬场的车来的时候,太阳正毒。两人抬着二叔往车上送,他骨头轻得像捆干柴。火化炉的烟筒冒烟时,大明在门口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坛,红漆掉了好几块。小明摸了摸坛口,突然想起二叔曾把攒了半年的硬币塞进他书包,说“买铅笔”,硬币硌得书包底沉甸甸的。 下葬时没烧纸,没磕头,连句“一路走好”都没有。村里人背后嚼舌根,说这俩侄子心比石头硬。可没人知道,大明结婚那年去借彩礼,二叔从炕席下摸出个布包,数了半天说“我就这点养老钱”,转头却把钱借给了村西头打麻将输光家底的老王;小明孩子满月想请二叔帮忙看几天,他坐在牌桌前头也不抬:“我老胳膊老腿,管不了小阎王。” 迁坟那天,公墓的风比荒坡温柔。大明从兜里摸出包烟,拆了两支插在坟前,烟丝被风吹得簌簌掉。“二叔,对不住。”他声音低得像蚊子哼。小明蹲下去用袖子擦墓碑上的灰,“以后清明我带酒来,你以前爱喝的那种。” 墓碑是新打的,青石板上刻着“叔父某某之墓”,名字旁边的生卒年月,是小明查了户口本才填上的。他手指划过“1967-2023”,突然想起二叔50岁生日那天,喝醉了坐在门槛上哭,说“我这辈子,活成了个笑话”。当时他觉得烦,现在才明白,那哭声里裹着多少没人听的孤单。 风卷着烟味飘过来,大明和小明站在墓前没动。远处有小孩追着蝴蝶跑,笑声脆生生的,像极了当年他和小明在二叔院里追着蜻蜓跑的样子。那时候二叔总坐在屋檐下看着他们笑,手里摇着蒲扇,扇面上的“福”字磨得快看不见了。 插在坟前的烟烧到了头,火星晃了晃,灭了。风里好像有个声音叹着气,又好像没有——就像二叔这辈子,那些没说出口的疼,和没被接住的好,终于在这方墓碑前,轻轻落了地。
猜你喜欢
今天参加了这辈子最冷清的一个葬礼,只有4人。我好友的父亲昨晚去世了,今天从养老院
2025-12-02
花的富贵
没想到采访把家里的爱之瞒全扒出来了!父亲本来笑着说“我家儿子最老实”,结
2025-12-02
石台上静思人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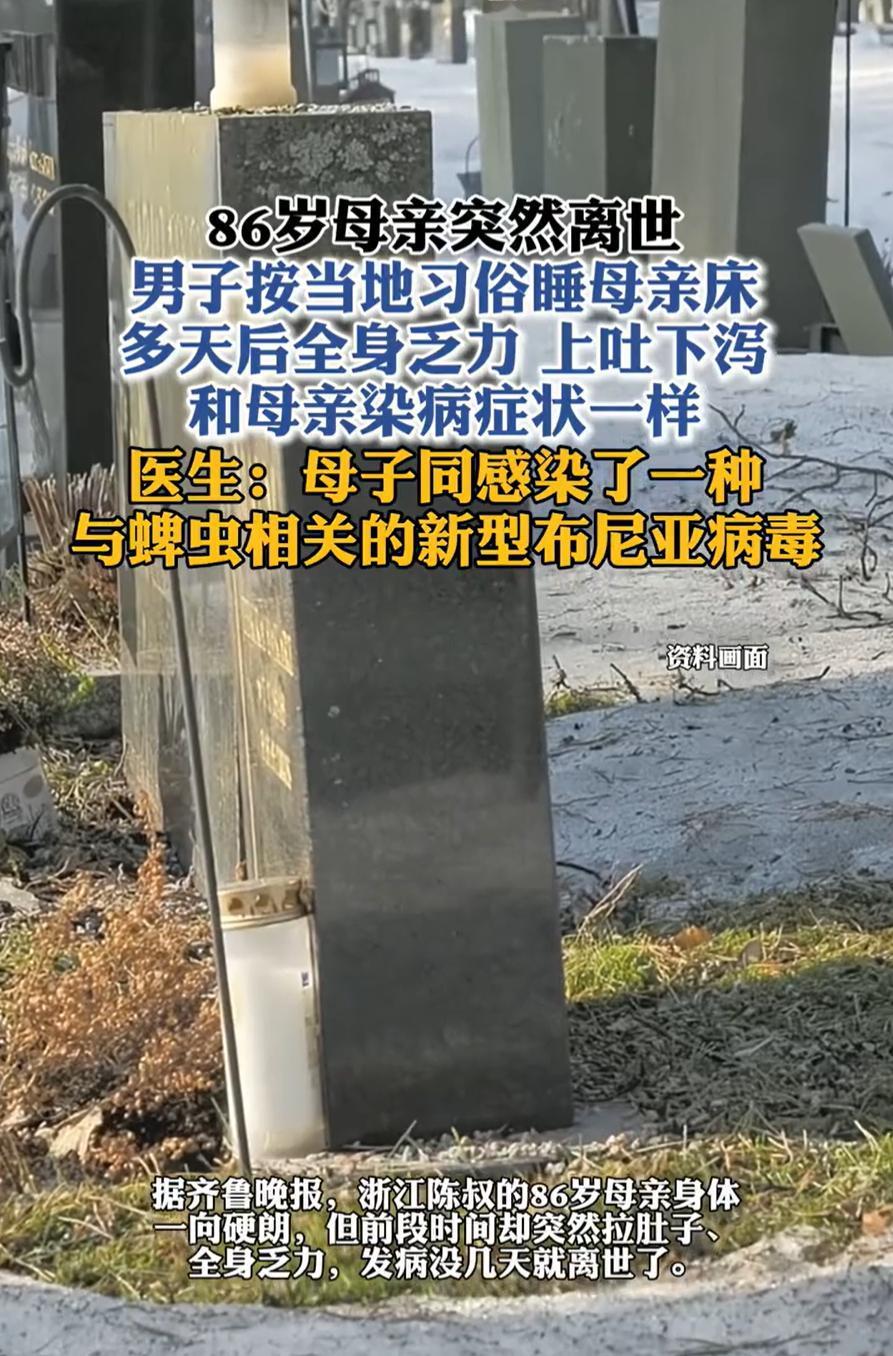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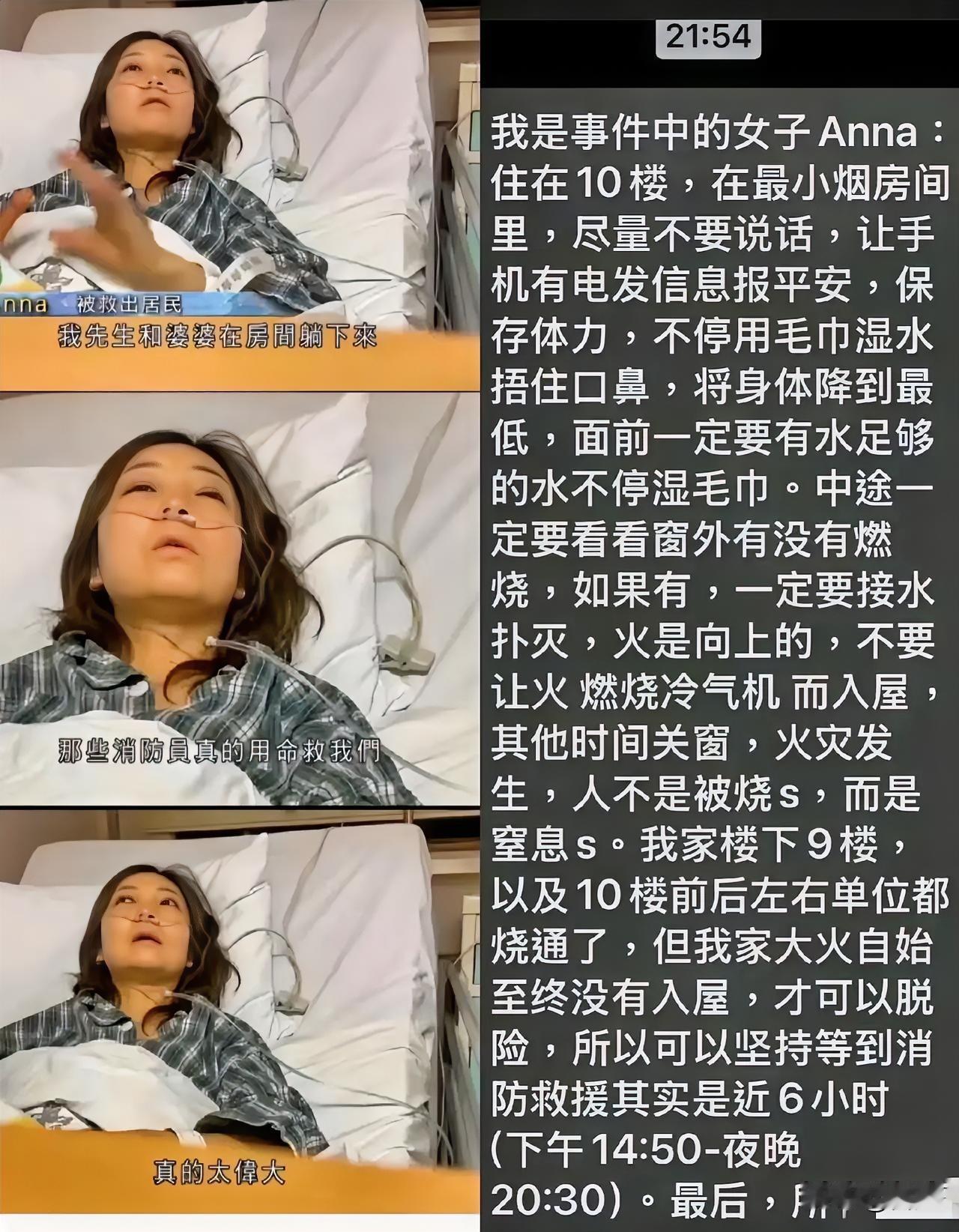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